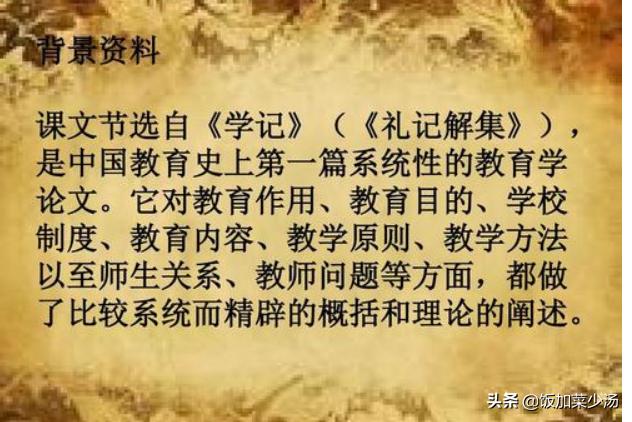洪承畴_洪承畴结局
是李氏(发妻,与后世名臣李光地同族)和刘氏(清廷所赐之妻,与李氏共侍一夫)
洪承畴的母亲傅氏读过书,知书达理,教子极严。承畴从小在母亲的教导下,攻读诗书。他聪明好学,七岁在本村的溪溢馆受启蒙教育。据说,八岁那年,洪承畴外公傅员外去世,母亲带他前去送殡。主持丧事的人问他们有无祭文,母亲摇头,他却张口说有。
洪承畴,崇祯十二年任蓟辽总督,领兵关外。崇祯十五年,于松山战败被俘,寻降于清,是最早降清的明朝重臣。松山失利闻于北京,君臣咸谓洪承畴必死,崇祯皇帝为之辍朝三日。
从洪承畴降清算起,投降问题横穿两朝(崇祯、弘光),令人焦头烂额。对于视“名节”为压箱底之宝的明朝来说,是沉重打击。但杨士聪却有别致的见解:
商周之际,仅得首阳两饿夫。北都殉节,几二十人,可谓盛矣。
自开辟以至于今,兴亡代有,万无举朝尽死之理。 首阳两饿夫,指伯夷、叔齐兄弟,他们都是商末孤竹君之子,武王伐纣后,耻食周粟,饿死首阳山。杨士聪说,较之商亡仅两人殉之,北京之陷有近二十人死节,还有什么不满意呢?兴亡代代有,也并未见过满朝文武全都死光的情形。
他说的乃是实话。跟过往比,乃至包括后世,明代士大夫的“名节”真是最过硬的了。明末殉国者之多,数量或抵得过以前历代总和。弘光政权幻灭后,殉国者成批涌现,仅本文提到的一些人,如史可法、左懋第、祁彪佳、顾杲等,后都自尽而死。虽然我们知道此一现象深受名教影响,但对死难者本人,我还是葆有很大的敬意;因为曾经考察过他们的事迹、思想以及时代背景,从而了解做出那样的举动并不都是出于迂腐。言及于此,也不能不从另一端感到些困惑。例如降清且助其平定中原的洪承畴,当时与吴三桂是一文一武两个头号“大汉奸”,但二百多年后,这种评价消失了,而代以“功在千秋”。孙中山有《赞洪文襄》一诗,称道他“满回中原日,汉戚存多时”;他还这样回答洪氏后人的提问:
余致力唤起民众推翻满清,目的在于推翻其腐败帝制。洪文襄降清,避免了生灵涂炭,力促中华一统,劳苦功高。
政治家思路果然实用。不过“满回中原”、“力促中华一统”或有之,“避免了生灵涂炭”则是没有的事,了解过清兵南下史的读者,心中都有一本账。关键是,历史究竟有无一定之理?是否能以结果论(实利)而朝秦暮楚?何况对洪承畴的这一评价,每一句我看亦很适用于吴三桂,为什么不把他也一道“平反”呢,是因他后来又举兵叛清吗?再有,这样评价洪承畴,置当年快意嘲讽洪承畴、为之杀害的少年英雄夏完淳于何地?这都令人困惑。
世间历来有“英雄”和“普通人”之分。我觉得恰当的态度是,对英雄应有英雄的尊重,对普通人也应有普通人的尊重。这不同的尊重,各自体现了一种社会公正与善意。但在中国,有时两种尊重都不存在。
作为个人行为,投降或不投降,受制于每个人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与追求,以及气质、个性等等因素,这些方面千差万别,既无一定之道理,也很难一概而论,该褒该贬,要结合每个人具体情况来看。
个人行为之外,还有一个国家伦理层面,我们需要讨论的也就是这个层面。国家伦理,作用在于鼓励、引导、规范社会和人民价值观,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,以及怎样做符合社会的共同利益。就此而言,投降不论何时何地,都不是国家所愿面对的情形,因为它与失败相联系,是不幸的境地。但在不赞赏的同时,能否基于现实,有所容纳、谅解与接受,对国家伦理而言,却是有关理性、博大和善意的更深刻考验。
其实,以我们知道的论,洪承畴投降似乎未曾如何“避免生灵涂炭”,尤其在清兵入关后,北方所以基本未闻屠戮,只因各地望风而降、未加抵抗,而南方,凡不肯降的地方,都发生大屠杀——比以后的日寇严重得多,日寇搞了南京大屠杀,满清则起码搞了扬州、江阴、嘉定三次大屠杀。故而,非得称赞洪承畴“功高谁不知”,大概只能落在“力促中华一统”、“满回中原日”这层意思上。用比较俗白的话讲,洪承畴投降,好就好在让中国版图大大扩张了。这,一是结果论,二是实利论——因有如此的结果和实利,我们对那件事便抱了好感与好评。京戏有《洪母骂畴》,演传闻已殉国的洪承畴,突然归家,母亲见他身着“胡服”,不由怒骂。这情节纯属演义(他的高堂跟他到了北京,过得好好的,顺治九年卒 ),但孙中山诗中“安裔换清衣”的句子,却与剧情构成奇异的反差,“换清衣”为洪母所骂,在诗句里反而有了“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”的自我牺牲气概,以一人之忍辱换来全体汉裔的平安。
历史,真是“此一时,彼一时”。
有趣的是,在洪承畴身上,不光后来汉人算糊涂账,满清出于本身需要也搅浑水。本来,所谓洪承畴劳苦功高,起码对满清而言确实如此。他的投降,是满清在关外时取得的重大突破。入关后,在搞定南中国过程中,洪氏更居功至伟。江南既下,洪承畴便受命为江南总督,在这抵抗最激烈的区域,充分发挥才智以及本身为“南人”的种种优势,软硬兼施,宵旰吐握,为清朝啃下这块硬骨头做出不可埋没的贡献。之后,领衔平定西南那终极之战,把南明小皇帝朱由榔逼入缅甸只差捉到手,因病不支,乞休,返京后一年多病故。自归降至终,洪承畴对清朝来说可谓“死,而后已”了。然而乾隆四十一年(1776),他却被清朝列入《贰臣传》。这个“贰”字怎讲?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“忠贞不贰”,洪承畴原为明臣、后降满清,显然没做到这一点,所以便“贰”了。这种情况,倘由明朝贬为“贰臣”还差不多,到头来竟是清朝给了他这样的评介。当然,“贰臣”还不是“逆臣”,清朝另有《逆臣传》,里面是些更坏的人。再者《贰臣传》亦非专门针对洪承畴,凡是由明降清的官员都列在其中。为什么通通一棍打死?且看乾隆上谕怎么说:
庚子,命国史馆编列明季《贰臣传》……如王永吉、龚鼎孳、吴伟业、张缙彦、房可壮、叶初春等,在明已登仕版,又复身仕本朝,其人既不足齿,则其言不当复存,自应概从删削。盖奖忠贞,即所以风励臣节也。因思我朝开创之初,明末诸臣望风归附。如洪承畴,以经略丧师,俘擒投顺。祖大寿以镇将惧祸,带城来投。及定鼎时,若冯铨、王铎、宋权、谢陞、金之俊、党崇雅等,在明俱曾跻显秩,入本朝仍忝为阁臣。至若天戈所指,解甲乞降,如左梦庚、田雄等,不可胜数。盖开创大一统之规,自不得不加录用,以靖人心而明顺逆,今事后平情而论,若而人者,皆以胜国臣,乃遭际时艰,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,辄复畏死倖生,降附,岂得复谓之完人?
被点名的降臣,情形并不一致。像吴梅村,虽然归附却悔意颇浓;像洪承畴,则并不三心二意,始终着实用命。对此,朝廷本当采取不同政策,区别对待;结果一视同仁,洪承畴虽“鞠躬尽瘁”,也仍然落个“贰臣”下场。所以这么搞,乾隆倒也打开天窗说亮话:当时为了得中国“开创大一统之规,自不得不加录用,以靖人心而明顺逆”,如今,“事后平情而论”,则叛变行径不能鼓励,而要“奖忠贞,即所以风励臣节也”。
这样,有关洪承畴其人,就形成不可思议的怪现象——他所投靠的一方,后来在不屑、鄙夷中将他一脚踢开;而他所背叛的一方,后来反而对他赞赏有加,认为可以名留青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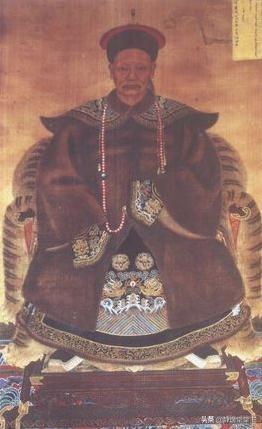


站在今天的角度,洪承畴是一个拥护国家统一的“英雄”,但站在明末清初的那个特殊时代,洪承畴的“三观”已经粉碎,完全违背了当时的社会导向,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大骗子,所以他才会被清乾隆列入“贰臣传”的行列。
当然,乾隆的行为有过河拆桥的嫌疑,很不地道。洪承畴为了大清能够打下江南,是做出了一份很大的功劳的。
如果没有洪承畴在江南奔波、招降,清军想拿下江南不一定有那么快。而乾隆为了收买江南汉族士族的心,将他一巴掌拍死,恐怕洪家后人都要羞愧死吧!
不过洪承畴没有什么可以洗白的,在他接受了皇太极劝降的那一刻,他的脸谱化就已经注定,不管他此前为了大明朝付出了多大的努力,一切化为泡影。
因为作为历史人物,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,而是尽可能的还原他所处的社会环境,洪承畴的所作所为,严重违背了儒家提倡的价值观。
不忠:身为大明人,在松锦之战被俘后不思殉国以求仁,却转身投向皇太极的怀抱。
不孝:身为汉人,为了荣华富贵毅然加入清朝汉军镶黄旗,甘愿成为旗下一奴。
不仁:担任清廷的“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”,成为镇压南明反清义军的急先锋,先后破南京、宿松、宁国、徽州、南昌、南康、九江、瑞州、抚州、饶州、临江、吉安、广信、建昌、袁州等府,“江南众郡县以次定”。
不义:杀抗清义军领袖金声、黄道周、李守库、徐君美、石应琏、应璧等人,不留活口。
大骗子:欺骗了大明朝上至崇祯,下至普通百姓的感情,让大明朝上下都以为他已经殉国了,并给他建立祠庙祭奠他,一时之间让他成为天下人的“英雄”。
洪承畴还是有大才的,他不仅协助多铎平定江南,还在顺治八年(公元1651年)开始,以“经略大学士”的身份坐镇荆州,指挥清军对华中、华南的反清义军进行镇压,并完成了对两湖、两广、贵州的军事布局。
顺治十六年(公元1659年),洪承畴再次奔赴到云南,坐镇昆明,调度吴三桂等满汉八旗军对内地南明义军进行最后的剿灭。
事实上,自崇祯十五年,公元1642年投降皇太极开始,洪承畴就已经成为清廷的第一文人,他为清廷做出的贡献是远远大于范文程的,因为清军在平定长江以南的反清势力时,洪承畴一直是战略策划家,清廷的战术基本上都是他提供的。
所以,要真正给洪承畴一个定义,那就是满清平定天下的大明第一降人,大清朝的真正干将!